回汉中搭子:一趟列车上的乡愁与相逢_[MMKMMC]
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,像一句重复了千百遍的催促。我靠在窗边,看着窗外熟悉的关中平原渐渐被秦岭的轮廓取代。每次回汉中,这趟列车都像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,一头连着谋生的喧嚣,一头系着根脉的宁静。而这一次,我的旅程里多了一个词——“搭子”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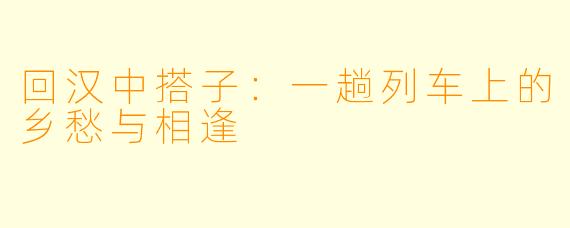
“搭子”,这个词在陕南的语境里,透着一种朴素的亲切。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朋友,却比路人甲多一份共渡一段时光的默契。它可能始于候车室里一句“你也是这趟车?”,也可能源于行李架上一次顺手的帮扶。在回汉中的列车上,“搭子”是一个流动的、温暖的共同体。
我的对面,就坐着这样一位“搭子”。一位约莫五十岁的大叔,脚边放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,里面大概是给家里带的物件或是打工的工具。我们相视一笑,算是打了招呼。列车开动后,他掏出几个橘子,不由分说地塞给我一个:“自家树上结的,甜得很。”剥开橘子的瞬间,那股清冽的甜香,瞬间冲淡了车厢里泡面的味道,仿佛把汉江边的湿润空气带到了眼前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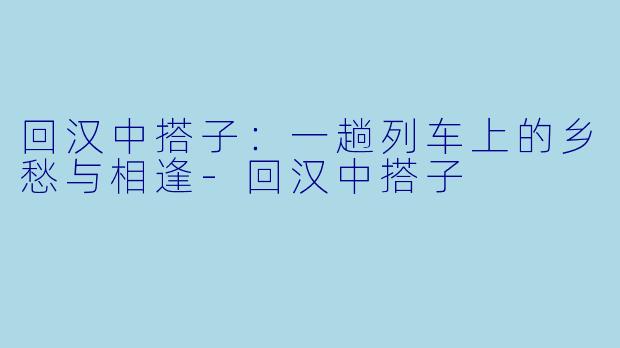
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。他问我:“娃娃,在西安做啥哩?”我说是上班。他点点头,眼神里是过来人的了然:“都一样,往外跑。就是这心里头,老惦记着咱汉中的热面皮、菜豆腐。”就这一句话,我们便成了“搭子”。我们聊起汉中即将到来的春天,聊起油菜花海如何从平坝一直铺到山脚,聊起老街哪家的核桃馍最酥香。我们甚至不用知道彼此的名字,但“汉中”这个共同的地理坐标和精神故乡,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这几个小时内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车厢里,这样的“搭子”组合随处可见。有一起在外打工、结伴回家的兄弟,一路上分享着收获与不易;有带着孩子的母亲,邻座的姑娘自然地成了帮忙照看的“临时搭子”;还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,围在一起用乡音热烈地讨论着什么,他们是同学,更是归途中最坚实的“搭子”。
列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,光明与黑暗在窗外交替。我忽然明白,“回汉中搭子”不仅仅是一个同路人,他更像一面镜子,照见的也是我自己的乡愁。我们分享的不仅是食物和空间,更是那份对同一片土地的眷恋,对“回去”这个动作的共同期盼。在这段被轨道丈量的归途上,孤独被稀释,焦灼被抚平。我们因为“回汉中”这个朴素而强大的目标,短暂地结盟,相互印证着归途的意义。
当广播里响起“前方到站,汉中”时,车厢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。大叔开始收拾行李,对我笑着说:“到了,还是咱汉中的空气吸着舒坦。”我们随着人流走下火车,在出站口互相道别,没有留联系方式,只是简单地说声“走了哈”,便汇入各自的方向。
也许明天,我们就又是茫茫人海里的陌生人。但我知道,就在刚才,我们曾是彼此合格的“回汉中搭子”。这段共度的旅程,连同车厢里橘子的甜香和关于家乡的絮语,已经成了乡愁的一部分,温暖而实在。下一次回汉中,我依然会期待,在哐当哐当的节奏里,遇见下一个“搭子”。
![[MMKMMC]Logo](https://www.laiyuecy.com/logo.p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