羊牯岭搭子_[MMKMMC]
羊牯岭没有羊,至少我从未见过。岭上多的是盘根错节的古榕,和一条被脚步与岁月磨得温润发亮的青石阶。所谓“搭子”,原是城里人时髦的说法,指那些因特定目的结伴的、淡于友情的同行者。但在羊牯岭,在这晨昏定省的登山路上,“搭子”二字,却意外地浸染了岭南潮润的烟火气,生出别样的筋骨来。
我的搭子,是老陈。我们相识于三年前一个微雨的清晨,在岭脚那棵大榕树下,彼此点头一笑,便默契地前一后踏上了石阶。没有询问职业,不曾交换姓名,只是每日清晨六点半,榕树下见。他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运动衫,我则拎着一个褪色的保温杯。最初的对话仅限于“早啊”、“落雨路滑”这般简短的提醒。我们保持着固定的距离——他在前,我在后,相隔约莫十级台阶。这距离刚好能听见彼此略显粗重的呼吸,却又不必费力交谈。脚步声、呼吸声、林间的鸟鸣,便是全部的交响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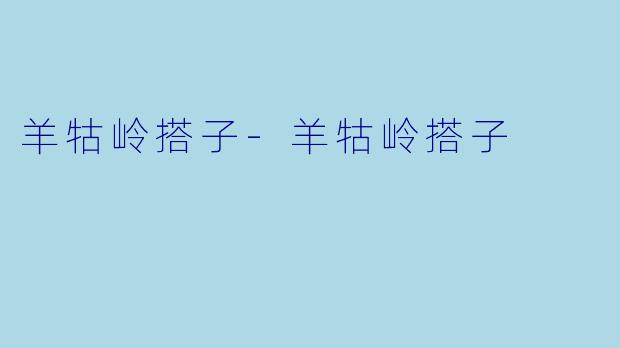
日子久了,这沉默的同行里竟也长出了细密的根须。我知道他会在第三处凉亭停下,用脖子上挂的旧毛巾擦汗;他知道我总在“摩崖石刻”那儿驻足,看一会儿斑驳的字迹。某日,他忽然在石刻前也停了下来,指着某个模糊的字形说:“这该是个‘云’字。”我凑近看,答:“我看像‘霞’。”我们便为这个无从考证的字争论了几句,最后相视一笑,继续前行。那是我们第一次“长谈”。
后来,对话的缝隙渐渐被日常填满。他聊起过儿子在北方读大学,抱怨过菜市场的猪肉又涨了价;我则说过阳台的茉莉开了,感叹过新修的马路吵人。话都很碎,像石阶缝里钻出的青草,不成篇章,却生机勃勃。我们知晓了彼此生活的轮廓,却依然恪守着某种心照不宣的边界,从不过问更深的东西。生病或出差,几日不见,再遇时也不过一句“前几天没来?”对方答“是啊,有点事”,便接续上原有的节奏。这份情谊,如同岭上的空气,清冽而不过于亲密,存在得自然而然。
最记得一个闷热的夏日,我因家事心烦,登山时步伐沉滞。行至半山,他突然在我不远处停下,并不回头,只望着山谷里蒸腾的雾气,说:“你看那雾,聚得快,散得也快。没什么是过不去的。”说完便继续向上走。我愣了一下,望着他湿透的后背,眼眶忽然一热。那句话,他未曾解释,我亦未曾道谢。一切恰如岭上适时吹来的一阵风,拂过便是慰藉。
这就是羊牯岭的搭子。我们因岭而聚,缘阶而行。下了岭,便汇入山脚下那个庞大嘈杂的菜市场,各自买各自的菜,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。或许某日,其中一个不再出现,这段关系便会无声地终结,如同石阶上被新雨冲刷掉的昨日足迹。但此刻,在这蜿蜒的青石路上,两个沉默的背影,一前一后,用脚步丈量着晨光,用呼吸应和着林涛,便构成了对抗城市孤寂的最朴素同盟。我们不是朋友,却共享了一段又一段向上的路程;我们只是搭子,但这偶然的、持续的同行,本身就已是一种温暖的深意。
![[MMKMMC]Logo](https://www.laiyuecy.com/logo.png)